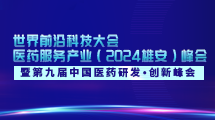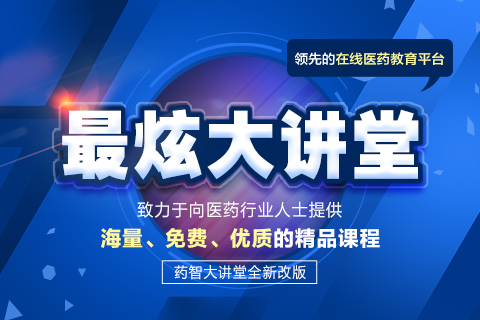新药探索没有止境,挑战SCLC还需更多努力!
日前,罗氏发表了III期SKYSCRAPER-02研究的最新结果。该项研究评估了抗TIGIT抗体tiragolumab联合已获批的PD-L1抑制剂Tecentriq和化疗,作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(ES-SCLC)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的疗效。
结果令人大失所望。在490名接受SCLC一线治疗的患者中,无进展生存期(PFS)没有得到明显改善,未达到共同主要终点,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,总生存期(OS)的数据也不太可能具有统计学意义。
错过两个主要终点,让罗氏试图在SCLC领域“梅开二度”成为泡影——此前,罗氏正是凭借Tecentriq+tiragolumab这对组合,在竞争激烈的非小细胞肺癌(NSCLC)突出重围。
Tecentriq是首个在ES-SCLC领域中展现出生存益处的癌症免疫疗法,联用tiragolumab可同时抑制TIGIT和PD-L1/PD-1通路,能达到1+1>2的抗肿瘤效果。NSCLC上的成功,让罗氏看到了该组合的潜力,但棘手的SCLC领域却不是那么容易挑战成功的。
罗氏的首席执行官Bill Anderson在上月的电话会议中讲道:“即使出现了负面结果,仍然不会削弱我们对于整个计划的信心。”
NSCLC成功在前
2020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(ASCO)癌症会议上,罗氏公布了一项名为CITYSCAPE的II期试验的早期数据。该研究旨在评估Tecentriq和tiragolumab联用,对比Tecentriq单药,作为PD-L1阳性转移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疗效和安全性。
援引当时的数据,罗氏的该组合疗法可以缩小31%的转移性肺癌患者的肿瘤——这一获益是单独使用Tecentriq的两倍。
同时,根据CITYSCAPE的随访数据,在ITT(intention-to-treat)人群中,联合治疗组达到了两个主要共同终点——客观缓解率 (ORR) 为31.3%(Tecentriq单药治疗为16.2%),PFS有43%的下降,联合治疗组中位PFS为5.4月(Tecentriq单药治疗为3.6月)。
在高水平PD-L1(TPS≥50%)人群中,联合治疗组与Tecentriq单药组的ORR之间,更是达到55.2%比17.2%的差距,联用还把疾病恶化和死亡风险降低了67%。在之后的六个月随访发现,联合治疗组对患者的ORR和PFS的改善持续存在。同时,两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。
CITYSCAPEII期结果,令业界对同时阻断TIGIT和PD-L1通路的联合疗法“浮想联翩”。
彼时,罗氏十分看好这一组合,声称其或许是一种解决癌症中未满足需求的新方法——TIGIT和PD-L1通路不同但可互补,tiragolumab在其中可起到免疫放大器的作用,提高PD-L1的响应,协同激活T细胞以及增强NK细胞的抗肿瘤活性。
事实上,PD-(L)1一直存在着低响应问题,其单药有效率仅为20%-30%,其原因是肿瘤不止一种免疫逃逸的途径。因此,解决低响应问题一直是众多药企在寻求PD-1/PD-L1赛道突破的着力点,尤其是在当下明星药物Keytruda和Opdivo牢牢把握市场份额的前提下,后起之秀们看好联合疗法。
罗氏为Tecentriq制定一系列的开发计划,联合tiragolumab就是其中尝试之一。
2021年年初,tiragolumab获得FDA授予突破性药物资格(BTD),用于联合Tecentriq,一线治疗肿瘤呈现PD-L1高表达、无EGFR或ALK基因组肿瘤畸变的NSCLC患者。
SCLC研发遇“冷”背后
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中国癌症报告,肺癌仍是我国造成死亡率最高的癌症。而放眼全球,肺癌也名列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前列。
按照病理来分,肺癌可分为SCLC和NSCLC两种,其中SCLC是肺癌中侵袭性最强的亚型,约占肺癌的15%-20%。
在SCLC和NSCLC两个领域内,药物研发“受欢迎”的程度可谓是冰火两重天。根据数据,已获批上市的覆盖NSCLC适应症的药物多达164个;相比之下,SCLC的情况就比较惨淡,获批一线治疗的药物寥寥无几。
至于在研项目,SCLC更是比NSCLC差了好几个量级。
当然,NSCLC占比肺癌85%的情况,也是导致各个企业扎堆,变相冷落SCLC的原因之一。但两者对比如此悬殊,众多药企挑战失败,更大的问题还在于SCLC的复杂性。
SCLC的生长速度较快,早期便出现广泛的远处转移,可将其分为局限性(LS)SCLC和广泛期(ES)SCLC,约2/3的患者确诊时候已处于ES。
自1980年以来,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一直是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标准治疗。SCLC的肿瘤突变负荷(TMB)在所有实体瘤中均处于中高水平,虽然其对铂类药物敏感,客观有效率高,但是很容易产生耐药性问题,使得SCLC更易复发。公开数据显示,SCLC患者的两年的OS率不足5%。
当SCLC复发之后,治疗方案更为有限,在不考虑3、4级的严重不良反应情况下,标准二线化疗的反应率仅为24.3%,反应持续时间(DOR)约为14周。
谁在重燃SCLC的新希望?
SCLC中存在多种免疫细胞浸润,暗示着免疫逃逸和抑制或在SCLC的发生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。
免疫疗法为SCLC患者带来新的机遇和希望。而IMpower133和CASPIAN两项研究,更是为SCLC免疫治疗奠定了夯实的基础。
2018年的世界肺癌大会(WCLC)上,罗氏公布了IMpower133的研究结果,与标准化疗相比,Tecentriq联合化疗将中位OS延长了2个月(12.3 vs 10.3个月),降低30%的死亡风险。12个月的OS率,Tecentriq联合组为51.7%,化疗组为38.2%。两组不良反应率相当。
这一结果堪称重磅,打破了SCLC领域近30年的“沉寂”。2019年3月,FDA批准Tecentriq联合卡铂和依托泊苷作为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。
也正是基于此,罗氏备受鼓舞,希望将这一成功复制到SCLC领域。这次,罗氏在原本的Tecentriq+化疗组合上,再加入tiragolumab。但不幸的是,备受期待的尝试在近期遭遇“滑铁卢”。
冲击SCLC新疗法的路上,罗氏并不孤独。2020年3月,阿斯利康宣布,FDA批准Durvalumab+化疗(铂类联合依托泊苷)可用于ES-SCLC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。该项批准是基于2019年的CASPIAN III期临床试验数据。
在2021年的ESMO(欧洲肿瘤内科学会)年会上,CASPIAN研究更新了生存期数据:Durvalumab+化疗(铂类联合依托泊苷)的3年OS率达到了17.6%。
另外,在2021年的ASCO大会上,安进还公布了靶向DLL3的双特异性抗体AMG757的I期试验结果。DLL3蛋白在SCLC肿瘤细胞表面高表达,但在正常组织中低表达,而AMG757可与内源性T细胞和SCLC细胞结合,诱导T细胞增殖和连续裂解,随后肿瘤细胞凋亡。
I期数据令人兴奋,ORR达到20%,中位PFS达到8.7个月,具有持久的应答效果,且不良反应可接受。DLL3有望成为治疗SCLC的干预靶点。
此外,Opdivo和Keytruda也进军SCLC领域,作为三线治疗。但是在2021年,BMS和默沙东分别撤回Opdivo、Keytruda用于SCLC的适应症的审批申请。
写意君在3月上旬的时候,曾经报道过赛生药业在SCLC领域的进展。(阅读参考:赛生药业RRx-001进入III期临床,剑指小细胞肺癌铂类耐药难题。)其中,中山大学的张力教授对罗氏的Tecentriq获批评论道:“中位生存期才延长2个月,监管机构还是批了,不仅是美国,中国、欧盟等药监部门都批准Tecentriq的上市。因为我们在SCLC领域,实在是太久没有新的疗法出现了。”
SCLC存在着巨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,因为难,所以每一步都走得艰难,因而每一点进步都是弥足珍贵的。新药探索没有止境,胜败乃兵家常事,挑战SCLC还需更多的努力。

责任编辑:七斤
本文系药智网转载内容,图片、文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平台观点。如涉及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它问题,请与本网站留言联系,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。